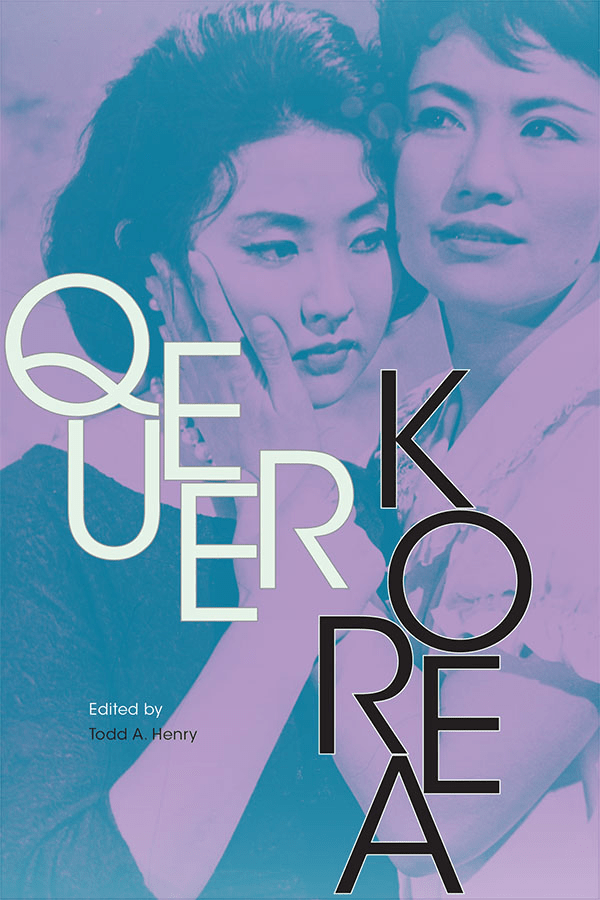
在本文中,我主张Yi Kwang-su的《Maybe Love?》与《Yun Kwangho》应被解读为殖民现代性的民族寓言,而非种族间浪漫爱情的描写。通过历史分析与酷儿理论的结合,我考察Yi笔下的孤儿意象、情感压抑与同性欲望如何揭示被殖民者主体性的分裂。这些文本借助象征结构与心理深度,同时表达了民族主义的渴望与帝国体制下的酷儿死亡驱力。
© River Lin 2025 For Queer Korea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第一部分 殖民现代性与民族寓言的历史分析
I. 重新设定解读路径:从跨种族欲望转向民族寓言
John Treat从种族视角解读《Maybe Love?》,认为“Mugil对Misao的情感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对异族认同的渴望,而非同性之间的情欲”(318页)。然而,此种解释将小说简化为精神分析式的浪漫文本,容易忽略其政治立场。相较之下,Perry与Chen的分析更具历史基础:Perry引用文学作为“铸造民族独立集体主体”的工具(Hwang 1999,第20页),而Chen指出Yi笔下的悲剧同性欲望“凸显出启蒙文明与民族建构计划的未竟之处”(Chen 2020,第128页)。我延续这一路线,主张《Maybe Love?》与《Yun Kwangho》应被视为民族寓言。两部作品中的情感强度体现的不是跨种族渴望,而是对殖民现代性失败的深刻关注。这些作品并未表达同化的意愿,而是呈现了被殖民主体对国家自主的追求之痛。

《Maybe Love?》中的孤儿隐喻与其说是私人忏悔,不如说是朝鲜殖民状态的政治寓言。主人公们,如Yi本人,在国家资助下赴海外留学。这一设定并不表明是自传式写作或单纯的同性情欲再现,而是Yi借熟悉经验建构民族寓言的手法。在《Maybe Love?》中,Mugil“十一岁时父母双亡,独自在世界上挣扎”(Yi 1918,第324页),象征朝鲜在殖民统治下的孤立与发育迟滞。他“渴望未来世代记住他的名字”与因“家庭与贫穷”所受的苦(325页),不仅是个人挣扎,更体现了在帝国压制下无法实现的民族意志。《Yun Kwangho》也采用类似结构。主角曾在日本拉面店打工,后获奖学金赴日留学,尽管学业成功却始终感到“空虚”“悲伤与孤独”(160页)。这些情绪反映出Yi在日本求学时的矛盾心理。透过这些“孤儿”角色,Yi构建出殖民异化与民族现代性被延宕的寓言。
Yi的象征结构从二元模式发展为三角关系。在《Maybe Love?》中,Mugil(象征被殖民的朝鲜)与Misao(象征文明日本)之间的关系,并非意味着跨种族同化,而是象征朝鲜对独立现代化的渴望。这种欲望并非“成为日本人”,而是模仿其国家发展路径。《Yun Kwangho》进一步将结构拓展为Yun(朝鲜)、Kim Chunwon(中国,象征“长幼关系”,Yi 1918,第162页)与P(日本)三者之间的地缘政治三角。作为在帝国都市求学的朝鲜人,Yun并未如Treat所说“认同异族”(Treat 2011,第85页),而是内化了殖民异化,进而转化为激进民族主义。他的情感破裂,恰恰展现了殖民现代性的极限。《Yun Kwangho》出版于1918年,恰在三一运动前夕(课程讲授,4月8日),显示Yi有意借此揭示投射于殖民者身上的情感最终如何走向悲剧。Yi运用个体化的心理叙述,非但不脱离政治,反而使其成为表达启蒙与民族救赎计划的媒介。那些看似个人化的苦痛,其实都根植于殖民情感结构与国家渴望之间的历史僵局。
II. 殖民现代性与现代主体性的心理展开
除政治与寓言式解读外,《Maybe Love?》亦可被视为围绕现代主体性展开的心理成长小说。Yi作为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现代主义小说先锋,显然借鉴了西方心理小说与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传统,尽管最终呈现的是一种悲剧性浪漫与现代性的残缺模型。正如Chen指出,西式浪漫爱情早已成为一种“跨语言实践”,深植于东亚文学之中(Chen 2020,第128页)。在《Maybe Love?》及其修订版《Yun Kwangho》中,“无回应的同性之爱”成为核心主题。仔细阅读可见,主线情节主要通过主人公情绪的剧烈波动推进。Mugil与Yun均从“欢喜与快感”(Yi 1909,第321页;Yi 1918,第159页)转入“孤独与疏离”(Yi 1909,第325页),情感异化甚至发展为心理危机。
Mugil并非全然被动角色。尽管他“不善闲谈”(Yi 1909,第323页),但仍主动拜访Misao。在门前迟疑时,他“故意加重脚步声”,以便让屋内的人听见(323页)。这一细节表现出Mugil的情感能动性。当被忽视时,他的间接引语转变为戏剧独白:“怎么会有人这样冷酷无情……我为你流血,你却连看我一眼都不肯?”(Yi 1909,第324页)。尽管这段心理线发展略显突兀,Mugil的痛苦暗恋仍体现出Yi借情感描写所呈现的殖民现代性。
Yi对情(qing)的描写还深入探讨了“羞耻”,其根源在于外貌与财富之缺失,这些是现代价值与社会可见性的象征。Mugil的自卑不仅因爱不得回报,更因其感知到自身在种族、阶级与性别上的劣势。他对Misao的渴望,虽受差异阻碍,但情感上却极为浓烈。Yi在《Yun Kwangho》中对情绪变迁的处理更为细腻。Yun对神秘人物P的迷恋,并非源于其与Chunwon间精神性的友谊,而是一种对“炽热而肉体的爱”的渴望(Yi 1918,第165页)。Yi更进一步描写了Yun对“亚洲现代女性气质”的主动拥抱:Yun使用“护肤水与美白粉”(Yi 1918,第167页)。这一女性化姿态具有象征意义,不仅是对异性恋规范的戏仿,也是酷儿男性主体性的自我建构。这并非简单审美偏好,而是殖民现代性下性别化欲望的体现。尽管爱未实现,Yun的情感与身体转化,体现出殖民现代性如何激发、塑造,同时又破裂情感与性别认同。
烈士情结或“背叛的抒情性”
关于Yi创作意图与其早期小说的历史意义,学界仍有争议。我反对将Yi早期作品简单贴上意识形态标签。他的作品中既有民族主义冲动,也包含模糊且矛盾的情感立场,我称之为“背叛的抒情性”——一种既肯定又复杂化民族忠诚的文学自我风格。虽然我们难以断定其真实创作动机,但本文已提出两种互补的解读路径:一为象征性的民族寓言结构,另一为心理化的情感经验。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常常受批评者的政治立场与历史距离影响。在《Maybe Love?》与《Yun Kwangho》中反复出现的“血书情书”意象尤为引人注目。尽管主人公被拒绝,但仍收到血书回信,这种罕见的象征行为反映出Yi对“残酷而无望的爱情”或“民族殉道”的深层执着。

我不同意Treat等人将Yi在青年时期想象为浪漫同化者的说法。即使在其后期政治立场发生重大转变时,这些早期文本中依旧保留着某种“殉道情结”的痕迹。汪精卫的案例提供了类似逻辑。他从革命者、诗人、国民党高官,最终转化为被谴责的合作者。但其诗作仍表达出通过个人牺牲实现国家和平的理想。同样,Yi或许并不认为自身“背叛”为完全投降,而是悲剧的历史选择。如胡兰成的《山河岁月》,Yi的小说也可视为一种文学自我塑造与修辞防御。但这些多层表达不应掩盖Yi早期小说中真切存在的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冲动。我们必须避免以“背叛”之眼回读文本——其美学语言与情感表达本身便展现出与国家身份及现代文学形式的深刻交涉。
第二部分 酷儿化校园男生亲密关系与亚洲酷儿死亡驱力的理论化
遵循Kadji Amin在《酷儿理论的谱系》中的批评立场,酷儿理论作为后现代批评方法,必须维持“无主体性”(subjectless),不应满足于复原明确的身份认同或作者意图(Amin 2017,第9页)。基于这一立场,我回到Roland Barthes在《作者之死》中的命题:文本的意义不应由作者的意图赋予,而应源自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遭遇(Barthes 1977,第148页)。因此,在分析《Maybe Love?》与尤其是《Yun Kwangho》时,我们必须避免将Yi Kwang-su的政治立场过度决定文本意义,而应采用如John Treat在解读Yi Sang的《翅膀》时所实践的酷儿理论视角,将时间性与情感置于传记确定性之上(Treat 2011,第85–86页)。正如Eve Kosofsky Sedgwick在其名文《偏执式阅读与修复式阅读》中所倡导,酷儿阅读应追求修复的可能,不仅关注酷儿抵抗了什么,更应思考它可能给予什么(Sedgwick 2003,第150–151页)。如果我们采取这一修复式方法来阅读,《Yun Kwangho》将显现为一部酷儿现实主义小说,真实捕捉同性欲望与其在20世纪初东亚文化语境中的不可能性之间的致命张力。
Yi构建出一种刻意无法解决的同性之爱,甚至可能故意模糊P的性别,以凸显这类欲望在社会与情感层面上所遭受的禁忌与压抑。若爱的对象为女性,通往浪漫满足的路径便不需如此秘密与苦楚。在现代同性身份尚未成为可识别历史形式的年代,东亚社会中的同性欲望往往被投入沉默。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不服从规范的主体”,他们的渴望无法被异性恋的叙事脚本所容纳。如前所述,人物的痛苦不仅来自欲望本身,更来自其无法言说的状态。在《Maybe Love?》中,Mugil体验着爱与苦的交缠:“他爱,他受苦。他的苦便是爱,爱便是苦。”(Yi 1909,第326页)而在《Yun Kwangho》的大学空间中,情感压抑转向身体表现。在与Chunwon疏远后,Yun唯一的慰藉便是偷偷注视街上的美丽男女:“在电车上偷偷看那些俊美的男孩女孩,是他唯一的安慰”(Yi 1918,第164页)。这种孤独不断深化,乃至于“故意将腿靠近她,只为了体会她温热的身体”(Yi 1918,第165页)。这种极端的孤独与性压抑正反映了东亚酷儿的生活处境,尤其是那些被迫隐藏身份的个体。Yi的描写揭示了:不论异性或同性欲望,性既是文化禁忌,又是情感爆发之地,在现代主义文学中成为“沉默之苦”的象征主题。
《Yun Kwangho》与《Maybe Love?》中的自杀情节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殖民与异性恋规范双重压力下,爱情、拒绝与自我价值之间的关系为何如此致命?文本明确地揭示了Yun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情感根源。他并非“为P而活”,而是“因P而活”(Yi 1918,第168页)。由于自认缺乏美貌、财富与智慧,他将P的拒绝视为对自身价值的最终否定。这种孤立、内化的叙述结构将他引向死亡——既是个人情感的终点,也是象征性的抗议。《Maybe Love?》中Mugil卧轨的自杀未能获得如此充分的心理动机,但在Yi的后期修订中,自杀行动不再是单纯戏剧化姿态,而成为对“无法承受之爱”的身体回应。在两个文本中,死亡既是自我毁灭,也是一种极端情欲的最终表达,是一种无法回应的语言。
若将此与女性自杀进行比较——例如Perry、Chen与Yang等人对双重自杀的分析视其为对父权婚姻制度的抵抗(Chen 2020,第127–128页;Yang 2017,第260–261页)——我们可以看到男性酷儿的欲望政治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在父权体制下,女性性主体性被抹除,而男性同性欲望则遭到激烈压抑。对“新女性”而言,性欲成为反叛父权的宣言;而对像Yun这样的“校园男孩”而言,亲密关系则成为通往破碎与死亡的忧郁路径。Yi所描写的Yun之脆弱,并非身份认同的宣告,而是对殖民现代性中欲望、承认与生存限度的现代主义沉思。
结语
通过本文,我提出Yi Kwang-su的《Maybe Love?》与《Yun Kwangho》应被重新理解为以情感、心理与象征结构所建构的殖民民族寓言和酷儿现代主义文本。与其将其作品简化为种族融合或浪漫幻想,不如说Yi借助情感过剩、主角孤儿身份与悲剧性自杀构建出了一套关于殖民压迫、民族渴望与情感现代性三者交织的复杂寓言。这些文本展现了殖民现代性如何在培养主体的同时制造其分裂,如何以爱与苦之名设下无法逃脱的历史陷阱。
發表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