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学期,我参与了历史系新生研讨会“明代中国的短篇故事”,我将分享我的阅读体会以及课外的衍生阅读。担任本次研讨会教授是 Prof. Schneewind。她也有中文名——“施珊珊”。

(上图:UC San Diego Department of History)
第一周,我们讨论了冯梦龙 “三言”之一《喻世明言·第十卷》——腾大尹鬼断家私。
首先我们对明代进行了断代。1368-1644。在历史分期上,明代在学术上称作“早期现代(Early Modern),这是为了对应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的概念;此外,又可以称作“中华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包括了明清时期,从政治角度命名。
《腾大尹鬼断家私》主要讲述了一个婚姻与继承的问题。年过八十的倪太守,相中出身于落魄书生家庭的梅氏,纳为妾室。梅氏诞下一子,倪太守弥留之际许下诺言,只要梅氏从一而终,他就能保证母子后半生生活无虞。面临的挑战是来自倪太守的嫡长子倪善继,他贪婪无度,想要私吞所有家财。经过中间人腾大尹的长袖善舞,梅氏之子倪善述分到了父亲埋在陋室的巨额银两,腾大尹也装神弄鬼地私吞了埋藏的千两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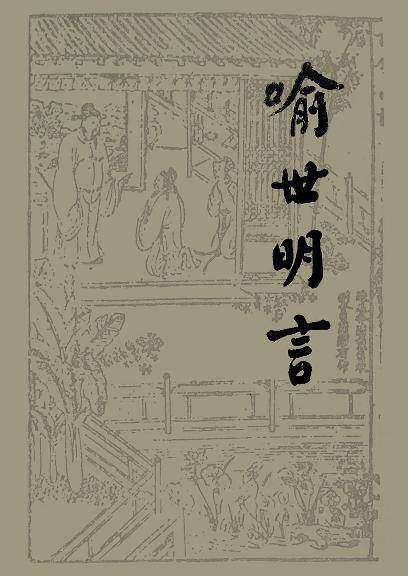
通过上课前的阅读,我关注到了三个点:
1)贞/节观念 2)继承制度 3)里甲制度(基层组织)
而课堂上我们着重围绕着“婚姻与继承”的主题来展开讨论,对于明代婚姻家庭的社会形态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是一个“夫权/父权/君权”统治下的“三纲五常”的男权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进一步,有心人会严谨地称作“一夫一妻多妾制”,这是更准确的。施教授对比了正妻(Primary Wife)和妾(Concubine/Secondary Wife)的区别。
正妻往往是两个家族的决定,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妻强调明媒正娶,而且要经过特定的仪式才可生效。作为家族利益的结合,妻子会将“妆奁/嫁妆(dowry)”带到夫家,在法律上作为其可支配的财产(与此相对的是“彩礼(bride price)”,男方支付给女方的礼金,与嫁妆数量是对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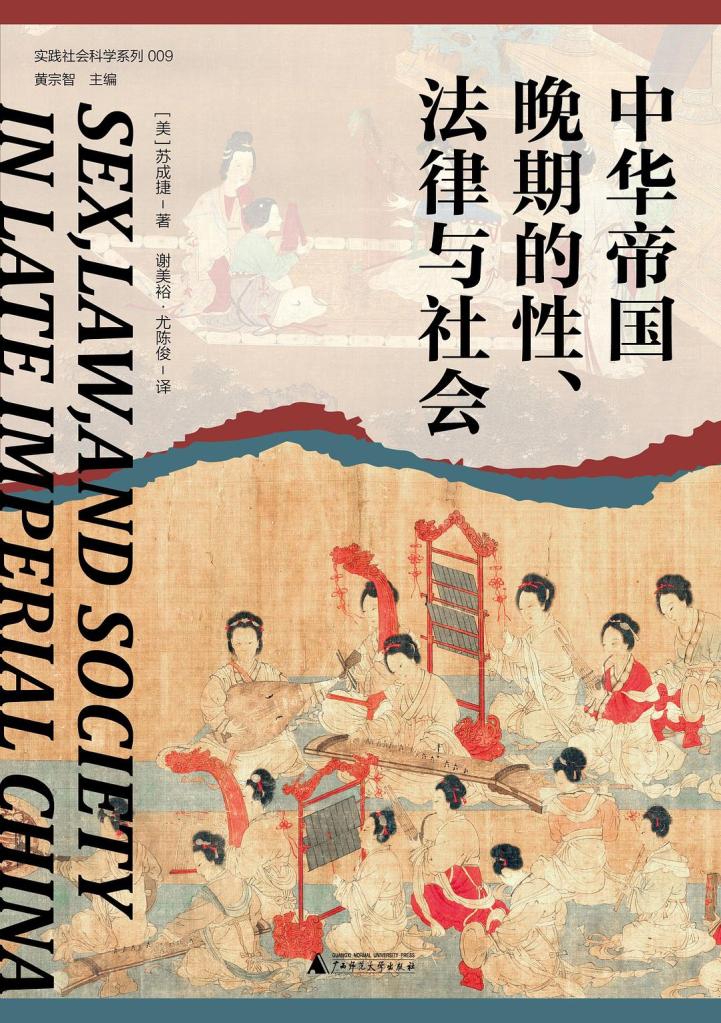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性与社会》中苏成捷(Matthew H.Sommer)写到:“‘以义交’谓依六礼而婚者。”“六礼”为君子之婚姻的基石,表示该婚姻既合法也合乎礼教。“六礼”的基本要素(《周礼》描述了其要点)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直至20世纪,这些仍是中国习俗中娶妻步骤的基本要素,只不过因时地差异而略有变化。这些步骤在中国帝制早期界定了贵族阶层中合法的婚姻类型,在中国帝制晚期则被扩展成一种指涉更广的、儒家关于家庭的正统观念的组成部分之一。”
夫妻之间的合法身份其实是女方的父权中让渡出来的,而夫妻之间性交的正当性原则是“礼”,子女对父母权威的服从,只有女方父亲的同意,才能赋予丈夫以权利。
妾就是来自于男性个人的选择,可以通过买卖取得,往往是歌女、丫鬟。这其中施教授也提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男性有权和家中女仆(maid servant)发生性关系。
苏成捷指出:“唐律的律文在言及主人与其家中女性奴仆发生的性关系时,所使用的字眼是听起来非常正面的“幸”字。”“主人向下跨越身份界限而与自家的女性奴婢发生性关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种类似“婚内豁免权”的制度,保障了主人的此种性特权”。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性与社会》一书中,斯坦福大学的苏成捷详细介绍了这一问题的历史变迁,在清代由于平民阶层受到贞节观念的普及,主人被剥夺了这个性特权。但在明代,主仆之间的行为视作“良民”和“贱民”之间的关系,而缺少人身自由的贱民阶层不享受“一夫一妻”的法律约束。
接下来,施教授对比了正妻与妾所生的孩子们的异同。在继承权利上,合法的妻与若干妾的儿子,享有的继承权利是相当的。这与现代的“非婚生子女”享有的继承权一致,这是出乎我意料的(嫡长子继承制只存在于皇室及先秦时期)。在名义上,妾所生的孩子的法律上的母亲是正妻,而生母只是生理上的母亲。而在这则故事里,继承的合法性来自于遗嘱(will)、裁决(judge)、法律(law)。
在厘清了继承问题后,在婚姻问题上,我提出了“寡妇守节(chastity)”的话题。关于贞节问题,除了广泛印象中的封建糟粕这一标签外,实际上包含着性别维度上的历史纵深和现代遗留。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有识之士就已经讨论了古代中国贞节问题,如鲁迅全集中的《我之节烈观》,胡适随笔中《论女子为强暴所污》。(后高彦颐等人称陈东原等为五四史观)
“贞节”并非完全等同于“贞洁”,而是有具体的意涵,“贞(virginity)”是未婚女子守贞,“节(chastity)”是指寡妇(widow)守节,所谓从一而终。
未婚女子守贞,婚前性行为以及婚外性行为被视为“失贞”(直至今日亦如是),在明清特别是清朝,还有“烈女”这一说法:“面临王朝覆灭、异性侵犯(对女子而言)或丈夫死亡,自杀作为道德品格的终极表达成为风尚。明清两朝将几十万个道德楷模表彰为“节烈”,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而受到地方政府和儒家文人表彰的人数则更多。但在明清人眼中,最激烈的道德行为莫过年轻女子为未婚夫终身守节甚至殉死。” 在我校教授卢苇菁的著作《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中详细探讨了明清时期社会父权意识形态对未婚女子的束缚。

寡妇守节作为故事中出现的情况,在课上做了详细的探讨。卢苇菁指出:“儒家正统的性别价值观贯穿于国家法典、家训族规、教化作品,甚至通俗文学中,不仅对规范精英阶层而且对规范普通百姓的行为也起到了作用。” 正是明清之际,“寡妇守节从一种道德理想(admired virtue)成为一种道德实践。” 施珊珊教授指出,这种道德实践往往发生在上流阶级,也就是文中家财万贯的倪太守和出身士人家庭的梅氏,而在平民阶层,寡妇再婚是合法的且普遍的。正如卢苇菁所著:“节妇与贞女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虽然贞节是任何正派女子都应遵循的古老美德,但儒家从不反对未婚女子再次订婚。”
施教授罗列了寡妇再婚的考量(considerations):名声(reputation),包括家族的和个人的(purity);财力(money);知识(scholarship & management);生产能力(fertile)等等。综上,大部分的寡妇完全是可以被允许再婚。但是,“寡妇守节”作为一种道德理想(admired virtue),也成为了明清独特的一种道德风尚。我们常说的“贞节牌坊(arch)”(旌表),就是清政府为了嘉奖表彰贞女与节妇设立的。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性与社会》中《贞节崇拜中的寡妇:清代法律和妇女生活中的性与财产之关联》,和《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中《旌表和满族的民族身份》(18C-19C)两章对此有详细探讨。
發表留言